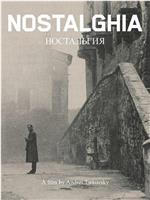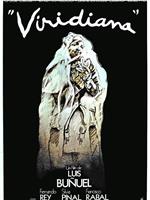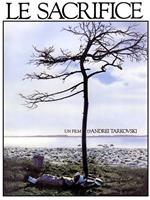冬日之光 (1963)
- 别名:冬之光 / 领圣体者 / Winter Light / The Communicants
- 豆瓣评分:
- 导演: 英格玛·伯格曼
- 演员: 古纳尔·布约恩施特兰德 / 马克斯·冯·叙多夫 / 英格丽·图林 / 古内尔·林德布洛姆
- 类型:剧情
- 语言: 瑞典语
- 地区: 瑞典
- 上映时间: 1963-02-11(瑞典)
- 片长: 81分钟
- 资源状态: 可播放
- 更新时间: 07-27 01:15
《冬日之光》下载资源
《冬日之光》相关推荐
《冬日之光》剧情内容介绍
《冬日之光》在线观看和下载
剧情内容介绍
冬日之光原名:Nattvardsgästerna,又名冬之光、领圣体者、Winter Light、The Communicants
埃里克森牧师在瑞典一小镇宣扬**的爱,认为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但围绕在他身边发生的事却弥漫着世界末日的气息,因为他与人全无沟通。上承《犹在镜中》,下启《沉默》的《信仰三部曲》中间作品,场景集中(室内剧形式),时间短促(发生在一天内),虽然简洁但传递出深刻的涵义。
发布于1963年。由英格玛·伯格曼执导,并且由编剧英格玛·伯格曼携幕后团队创作。集众多位古纳尔·布约恩施特兰德、马克斯·冯·叙多夫、英格丽·图林、古内尔·林德布洛姆等著名实力派明星加盟。并于1963-02-11(瑞典)公映的电影。
《冬日之光》评价
没有昵称 2024-11-03
布景简单,剧情简单,对话继续是一些不着调神学。不过这部的摄影感觉太简陋了:有个镜头是对准神父,慢慢zoom in到他的脸,然后神父失落地说,上帝抛弃了我,说完就再zoom out。看得我直感叹:这也太简单粗暴了吧……没有爱具体的人的能力难道不应该是神父界普遍现状吗,值得这么大做文章吗🤷(Max von Sydow演的男人因为看到新闻里中国人就要制成***于是就抑郁了这件事我倒觉得还挺合理,大概跟我因为美国人搞不好就要选***而有些emo一样,属于那个年代欧洲人**政治抑郁的一种。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政治抑郁,总有适合你的一款。伯格曼对意识形态整个不感兴趣甚至很厌恶,所以就随机选了一款而已。)
冰红深蓝 2020-03-15
"神之默示"三部曲中篇。1.风格极简而质朴,布光精妙,以静止镜头和小景别为主,摄影机对人脸的凝注一如既往。2.冷漠、疏离、傲慢、信仰动摇的牧师解答不了苦难与生死问题(由中国即将研制成功**引发的焦虑),亦无法接受玛塔对自己的爱。3.片尾教堂司事自承对耶稣受难时高喊的“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见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后两福音书则无此细节)的思考发人深省,身心的苦难与信-疑的纠结溢于言表。4.八分钟的玛塔对镜读信段落情真意切,中途插入的手中溃烂皮疹镜头则同质于耶稣圣痕。5.牧师发出天问后的一刹那,窗外耀眼的**兀自笼罩了他,一如**克[通往仙境]结尾的那道神秘圣光。6.牧师说,每当直面上帝,祂就会变成某种丑陋恶心的东西,如蜘蛛——恍若[犹在镜中]变奏。7.首礼拜详尽展示,末尾则仅有非**玛塔一人。(9.0/10)
Chardonneigh 2020-01-03
61年春天,伯格曼因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苏联最忌惮的国家竟是中国而非美国,便开始担忧以中国的**(regimented )情况会很轻**动一场核战争。实际上伯格曼并不太关心世界政治,瑞典在当时也采取了武装中立的**政策,比起核威慑,国家日益世俗化、科技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给传统宗教社会带来的冲击才是伯格曼想讨论的。《冬日之光》是当时伯格曼制作周期最长,片时却最短的电影,他对电影的苛刻程度更是前所未有,伯格曼摒弃以往精美的打光与追求形式感的摄影,试图呈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气质,为了追求神父更自然的焦虑情绪,不惜“使坏”差点毁掉与布约恩施特兰德的关系,一切偏执创作的背后都是伯格曼异常重视这部电影的表现,《冬日之光》也的确成为了他最深刻的信仰危机电影,哪怕它的确显得沉闷又无聊
圆首的秘书 2018-04-15
冬日之光中充满着恐惧和焦虑,但完全不见爱的踪影,初见人与人之间互斥关系的端倪。爱人说牧师最大的问题是“对**的冷漠”,他甚至无法说*别人,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坚持,但最后的结果是悲剧性的:教堂里甚至没有人愿意再去伪装了,仇恨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的***),信仰何处安放呢?
康报虹 2018-04-01
伯格曼一生不断地相信、质疑、否认、肯定、幸福、痛苦的回环纠缠和激荡,在他和上帝的“摔跤”过程中,他通过影片来表现他幽冥晦暗处的驳杂思想和宗教浩渺感:世人痛苦焦灼、上帝神秘莫测、灵魂低语无奈,许多潜伏在幽冥深处的哲学玄妙通过他的不可言说的**和丰富多彩的影像表达出来。
brennteiskalt 2016-07-10
在信念终于垮塌的黑暗时分,一束[冬日之光]倏忽照亮了牧师的脸。呵!上帝不是***亦不是上帝,怀疑才是。当结尾的钟声敲响,女主角跪下去祈求哪怕一丁点的信仰,我们很难不为之动容。这就是人类吧,在疑惑中苦苦寻觅着光亮。伯格曼不仅用他高超的语言、更用他的沉默轻松地摧毁了我。那是上帝的沉默。
蓝笔风 2016-02-27
人物反思力度惊人依旧,叙事简洁明了,甘纳尔和英格里德对“距离感”分寸拿捏好到位,从开头讲道对“他们”说到结尾说*自己,借了男女情感得失,**受难终极困惑的矛盾把人与人信任危机的悲剧核心表现淋淋尽致,牧师自我强迫的信仰之爱最终变得越发冰冷苍白,宛如冬日斜阳没有一丝人性温度。银幕重看
欢乐** 2013-11-16
#重看#古典、简洁、沉默、肃穆,德莱叶与布列松隐约可见;冬日之微光惨淡稀薄,恰如信仰之岌岌可危,**变化折射勾连心理转变;构图与镜头都很工整,与牧师职业&教堂氛围契合;他永远在书写亲情的疏离、神性的质疑,父亲的阴影像冬日的雪彻骨一生。
Lies and lies 2012-08-19
对白写得真好。两个很棒的段落:Lundberg女士念信,直面镜头难以逃脱;神父与Lundberg在铁轨前停车,神父说是他父母期望他成为神职人员,此时火车喷着蒸汽,头也不回地往前驶去。
有未始有始也者 2010-01-04
那個愛著牧師的**,給我一種除了牧師其他人都看不見她的錯覺。